导语:
修改发表于2025年06月26号 11点 阅读 3853 评论3 点赞16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今天是6月26日,想起了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由此,赤脚医生这一特殊群体应运而生。因为他们原本是农民,被选派到上级医疗部门学习一定时间之后回到本乡本土为父老乡亲提供医疗服务,这些人不是国家干部,不享受国家的补贴,是地道的农民。其次,在农忙时或早晚都要下地干活,一旦有人生病会随叫随到,不管在田里干活,还是在深夜睡觉的时候都会及时出诊。
我是一九七九年初被选拔进赤脚医生队伍的。那时节,崇明新海农场的杨树才抽新芽,灰白的枝条上迸出点点嫩绿,倒像是谁不经意间甩上的颜料点子。在春寒料峭的岛上,收拾好行李,连队的拖拉机手,把我送进了五七干校,由新海农场医院的内科主任医师顾耀章老师,给我们进行3个月的封闭式理论学习,期间还有别的科室主任医师进行授课,理论知识结束后,再进场部医院穿上梦寐以求的白大褂实习3个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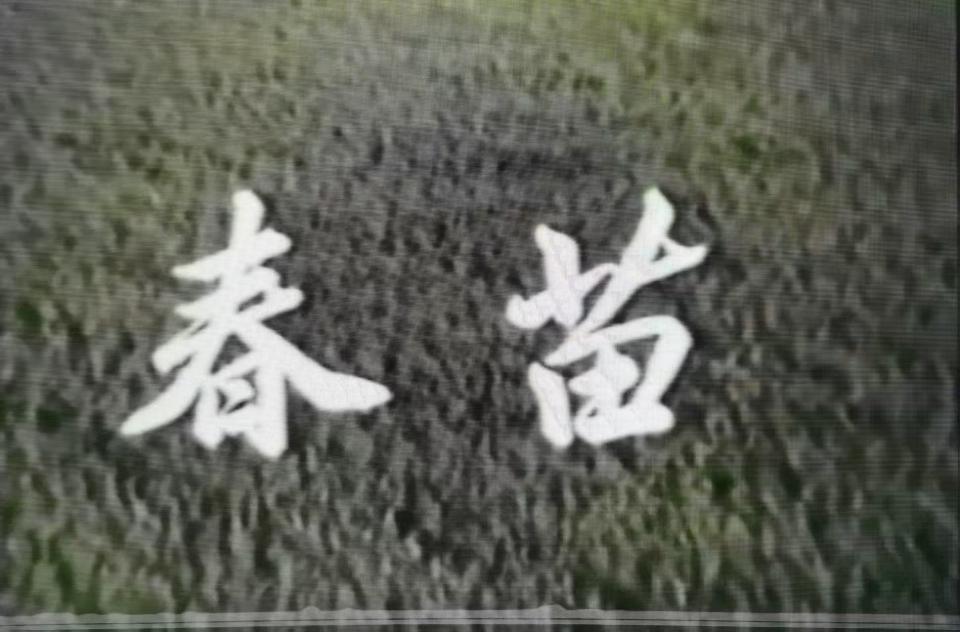
或许是我的父亲是海军军医,母亲是厂医,骨子里流淌着军医的血脉,而我的从医梦想打小就有了,1975年的一部电影《春苗》更加深了印象,田春苗的成长经历,深深地映在我的脑海里。培训不过半年光景,我胆大心细,无论学习,实践操作各科成绩都是优秀,很快就适应了角色。回到连队进入医务室工作,农忙时会挎着印有红十字的皮药箱,去到田头做一些应急救护处理。那药箱不轻,里头装着红汞、碘酒、阿司匹林、止泻药、纱布、胶布,还有几支青霉素——这在那时算是贵重药品了,须得营部卫生所的医生签字才能动用。药箱的背带勒在肩上,也感觉到了这份沉甸甸的分量!久而久之,军便服的肩头便磨出了两道白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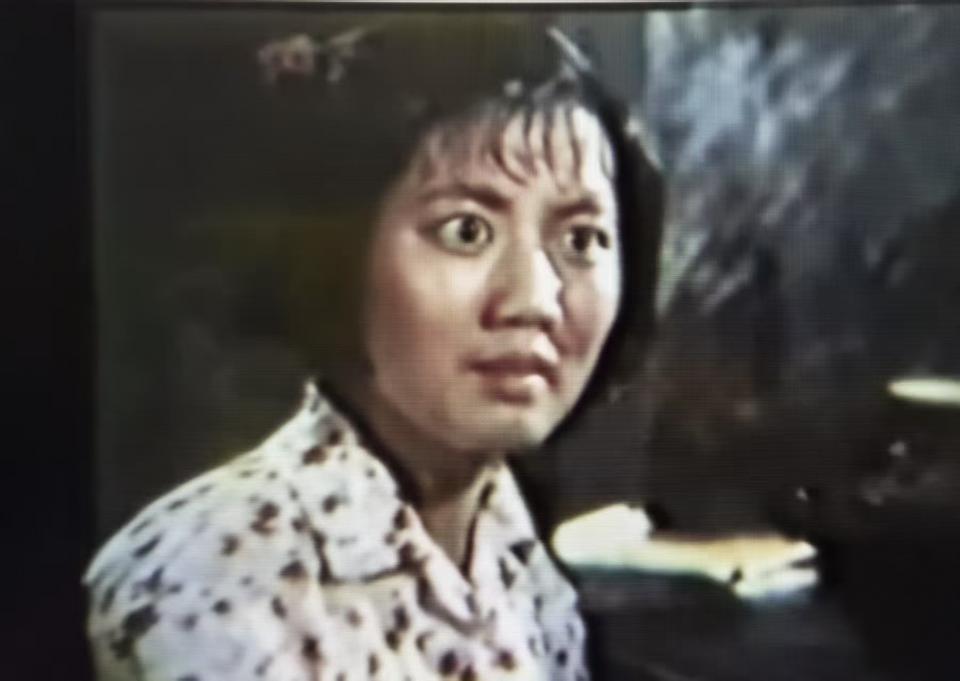
四百多号人的头疼脑热、磕碰损伤,全指着我和另外一个男生俩个二十出头的卫生员。起初自然是手忙脚乱的,后来便也熟稔了。高热的孩子,我给额上敷冷毛巾,配些退烧药;割破手的农友,我用碘酒给那伤口消了毒,缝合伤口包扎妥当;腹泻的老者,我发几片止泻药,叮嘱多喝盐水,严重者还给予葡萄糖静脉注射液。这些都是些寻常病症,不难应付。
连队里的也有人唤我“小医生”,虽知我不过是半路出家的赤脚医生,却也敬重。农忙时节,我便背着药箱下到田间。烈日当空,农友们弯腰插秧,汗如雨下。我时而在田里插着秧,时而随时准备处理蚂蟥叮咬、镰刀割伤或是中暑晕厥。药箱被太阳烤得发烫,打开时,里头蒸腾出一股混合着药味的古怪气息。有时帮着包扎完伤口,农友会咧开干裂的嘴唇笑笑,便又折回田间劳作去了。那笑容里的朴实,比任何感谢的话都来得真切。冬季农闲做水利工程~开河清淤,我们又会背着药箱去到工地,目睹农友热火朝天的挖泥挑泥,头疼脑热,伤腰蹩筋,也是临时处理一下,轻伤不下火线,有时候我会让农友休息一下,替她们干一会,战友情浓于水。药箱也是功臣。

营部卫生所的朱医生,是个部队复员回来的军医,我每遇疑难病例,便写转诊单送去他那里。他总是一面检查病人,一面向我讲解病理,眼神严厉,却藏不住对后辈的提携之意。他说,“治病如种地,急不得,也慢不得。”这话我记到现在。
难忘的是七九年冬天,连队里闹起了流感。家家户户都有高烧咳嗽的,我和另外一个卫生员日夜奔走,药箱里的阿司匹林很快见了底。没法子,只得熬了大锅的中草药和姜汤,挨家挨户送去。有时候忙的精疲力尽时,看见连部卫生室窗里的灯光,竟觉得那是我自己的体温在黑暗中发着热。
六年光阴,药箱的漆皮剥落了,我的医术也长进了不少。后来政策变了,连队里的人越来越少,只能合并转行,我被安排去了别的岗位。临行前,连队的老支书拉着我的手说:“小田啊,你是个好的小医生。现在要去果园小学做代课老师,相信你也会成为好老师。”我听了,只觉得眼眶发热。
如今回想起来,那药箱里装的不仅是药品,还有泥土——田间的泥土,沾在农友的伤口上,混在我的指缝里。泥土与血水、药物混在一处,竟成了我青春最鲜活的印记。
药箱早已不知所踪,唯有那泥土的气息,似乎还萦绕在我的指尖,历久不散。

信纸作者:林林总总

请选择你想添加的收藏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