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的三位初中语文老师
我的三位初中语文老师
新学年伊始,教师节到了。我的三位初中老师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一九六○年的秋天,我在南码头附近的上海市多稼中学上初中一年级。陈时谨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在我的记忆里,她曾经给我们上了一堂教学公开课。陈老师可能没有料到,在一位同学回答问题后,我不知道那来的胆子,会举手“补充”回答,好像打乱了她的公开课计划。她笑着马上叫我坐下,没有后语。这才让我感到自己的唐突。
我的初中二年级语文老师是姚痴存先生,五十多岁了,是一位和蔼的长者。姚老师说,解放前他就非常崇拜鲁迅先生。以前他曾经西装革履,后来将西装束之高阁,挂了起来。
他的女儿也是语文老师。他们父女之间,经常在小南门王家码头路口石库门房子的家里,交流语文教学工作的经验和体会。他夸女儿语文教得好,是学校里的先进教师。给我的感觉姚老师很自豪。
我记得那年的语文期末考试只考一篇作文,题目是《晨读》。我的考试成绩得了五分制的5分,但是在5的上面多了一个短横,也就是5减,离开真正的5分,还差一点。
季德兴先生是我三年级的语文老师。开学第一堂语文课,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潇洒地竖写了大大的“季德兴”三个字,很漂亮。他幽默地对我们说,他和南通大名鼎鼎的“蛇药大王”季德胜是本家。

第二排左三语文老师季德兴
季老师三十多岁,衣着很是艰苦朴素。老师经常穿着一条双膝各缝着一大块长方形补丁的裤子,站在讲台旁。
当时处于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上海市区每人每年只发二尺六寸布票,物资非常匮乏。但是像季老师这样经常穿着补丁裤子的知识分子是不多的。然而,在我眼里,老师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傲骨。
有一次,老师声情并茂地朗读叶圣陶先生《五月卅一日急雨中》一文:“从车上跨下,急雨如恶魔的乱箭,立刻打湿了我的长衫。满腔的愤怒,头颅似乎戴着紧紧的铁箍。我走,我奋疾地走。
路人少极了,店铺里仿佛也很少见人影。哪里去了!哪里去了!怕听昨天那样的排枪声,怕吃昨天那样的急射弹,所以如小鼠如蜗牛般蜷伏在家里,躲藏在柜台底下么?这有什么用!你蜷伏,你躲藏,枪声会来找你的耳朵,子弹会来找你的肉体:你看有什么用?
猛兽似的张着巨眼的汽车冲驰而过,泥水溅污我的衣服,也溅及我的项颈。我满腔的愤怒。”
这时的季老师以横眉冷对的神情,随手向衣服下面甩了一下,好像要甩去自己身上的泥水,以体现作者对“五卅”惨案的无声抗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季老师有时也会有些“阿Q精神”。老师在课堂上带着表情说:有一次他穿着有补丁的衣服乘公共汽车。站在他旁边有一位打扮时髦的姑娘,向他投来怪异的眼神。老师也向她“回敬”了不屑一顾的目光,并且抬起了自己高傲的头……
季老师曾经向我们介绍外国文学《牛虻》。那时《牛虻》一书深受青年学生的喜爱。我也很喜欢革命志士传奇的故事,佩服并且学习那些临危不惧、宁死不屈、为人民而战斗的英雄人物。
我没有认真地看过《牛虻》这本书,而是在学校图书馆的电视里看了苏联影片《牛虻》。影片主人公牛虻(亚瑟),开始由于他的幼稚、无知,受了教会的欺骗,连自己的情人琼玛,也因此出于误会而和他断绝来往。
后来,他逐渐成熟,成为一个革命者。当琼玛于十三年后重会牛虻时,依稀认出他就是当年的亚瑟。他俩并肩战斗,后来牛虻不幸被捕。在狱中,牛虻给琼玛的一封信里,写上了他们儿时熟稔的一首小诗:“不管活着,还是我死去,我都是一只,快乐的牛虻。”在刑场上,行刑队向他三次开枪。牛虻从容不迫,慷慨就义的影视形象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脑海之中。
虽然六十多年过去了,但是我的三位初中语文老师,仿佛依然在我眼前清晰地晃动着。
(注:您的设备不支持flash)
- 等36人点赞

精选留言
请选择你想添加的收藏夹
- 未定义0条内容 你没有登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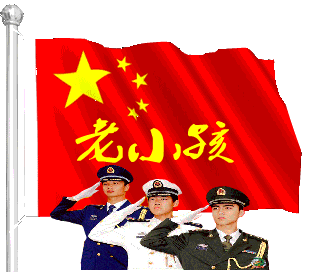 精彩不断,赞美无限。
精彩不断,赞美无限。


